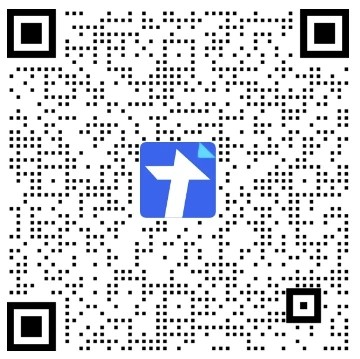平凡的母亲
平凡的母亲
文/姚艳秋
娘未进过学堂,今年74岁,慈祥、温柔、少言,她的一生,是极具韧性的一生。步入中年的我,脑海中时常浮现出娘为家庭奉献的几个场景。
我们姐弟三人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,那时候家里穷,到该上学时,因买不起书包,娘便东一家西一家去找碎布头,零零碎碎、花花绿绿,方的、圆的、三角的……什么形状的都有。娘很开心地把这些碎布片洗得干干净净,在床上摆出一个书包的样子,比画着书包的大小,估计着还差多少才能够缝成一个,然后把这些碎布片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到立柜抽屉里。隔一段时间,娘就再去找,数次以后终于攒齐了做一个书包的布头。娘白天要干农活,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做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。娘在灯下给我缝书包的模样我始终不能忘怀:她在煤油灯下打开一块块碎布头,摊开,抹平。接着,把布头严严实实缝在一起,顶针在娘的指间不停地转圈,针穿进布里时带着轻微的“沙沙”声,线脚走得又密又匀。昏黄的煤油灯把母亲的影子拉得很长,映在斑驳的土墙上,像幅被岁月揉皱的画。我们兄妹三人趴在床沿上,眼巴巴地盯着那些布片,嘴里不停地问还得几天做好,娘总是不厌其烦地说“别慌,快了,你们三个的一起做好。等做好了,都得好好上学。”娘没有读过书,却知道读书的重要。娘低头笑着,额前碎发垂下来,我伸手想替她拂开,却被她的手轻轻按住,那双手掌心有层薄茧,指腹被针扎出细小的红点,像落在雪地上的梅瓣。灯花“噼啪”爆了一声,娘抬手用剪刀尖挑掉,火苗又稳稳地亮起来,整个屋子总萦绕着煤油味混着棉布的味道。
数日后,一块块碎花布,在娘的手中,变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小书包。一年级开学那天,娘把书包斜挂到我肩上,我觉得那布面带着她的体温,暖暖的。此后的求学阶段,我背着娘缝的书包走过无数条路,直到走上三尺讲台。
后来,父亲考上了大学,在父亲攻读大学的两年时间里,娘带领我们独自生活,更是艰难。那时种地要依靠壮劳力和牲口,我家这两样都缺乏,因此,每到播种的季节,犁地、耙地、种地成了家里最大的困难,我们要等别人家都种完了,牲口闲下来,才能去借。大队的、邻居的、亲戚的、邻村的都借遍了。每次用完别家的牲口,娘总会把牲口喂得饱饱的才还给人家。最难忘的是娘给牲口铡草,她半蹲着,一手掀起铡刀,一手往里面续草,一起一落,看得我们心惊胆战,然后将铡碎的草收到一个竹筐里,端到牛的嘴边,等到牛吃饱再端走。这是我记忆中最清晰的一幕,直到现在,母亲半蹲的姿势和用力铡草的动作,还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,让我敬佩,让我心疼。农村人都指望着牲口过活,即使娘再细心照料,再借也有被拒的时候。借牲口的经历,是娘一辈子的痛,偶尔谈起,娘还会很伤感。记得有一次,父亲捎信儿说第二天要回来种地,娘力气小把持不住那些牲口,只有等父亲在家的时间把地种好,所以娘要提前把牲口安排妥当。可是那次,娘跑出去一天也没借到牲口。当天晚上,月亮好亮,娘决定去30里外的姨家借她家的一头黄牛,就把我、哥哥和妹妹锁在家里,懂事的我们没有闹腾,连平时娇气的小妹都没有哭闹,但是非常害怕,惊恐着熬到天蒙蒙亮,我们从门缝里看到娘牵着姨家的牛回来了,才算放心。只见娘把牛拴到院子里的榆树上,快到午饭时,父亲一到家,便和娘下了地,一口气把家里的地全犁完耙完。第二天早上,娘要去还姨家的牲口,父亲回学校,他走时再三叮嘱娘再坚持一年,等他毕业就好了。娘说没事,家里的事都交给她。娘没有抱怨,不管受了多少委屈,她在父亲和我们眼里,一直都是那么的平静、沉稳、不急不躁,她的坚强与隐忍,在那段时光里,给我们的感觉娘就是家里的一座山,她在我们就有依靠。
两年后,父亲毕业,分配到了县城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工作。父亲爱他的学生,娘像照顾我们一样照顾父亲的学生,不管谁病了,娘就会给他们熬药、喂药,耐心照顾。那时我们兄妹三人已读初中,父亲一人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,负担很重。我们心疼娘,有时责怪父亲天天领学生来家里给娘添负担,可娘总是那么一句“学生住校都想家,也没有山珍海味,让他们来吧”。父亲对那些学生也不嫌弃,还是会一拨一拨带到家里。天天如此,娘没有怨言,用她的行动诠释着对父亲事业的支持。而父亲也没有因娘没文化而嫌弃她,并常常教娘认字、写字。而今,娘已经可以顺利地读通一篇简短的文章,写下一段话了。这是父母对我们最好的人生教育,他们以身示范,教我们明白:唯有真情才能够长久。我时常回想起娘身上的点点滴滴,她对家庭的爱藏在生活的每个细节,温暖着我,也鼓舞着我。
精彩推荐
- “双11”购物,消费者成了“精算师”
- 我市召开高三复习备考工作座谈会
- 知识产权量质齐升 保护机制日益完善
- 采撷发展瞬间 见证时代新貌
- 驻马店市今年180名低收入妇女获“两癌”救助
- 稳投资、扩消费、促转型 前三季“两新”政策
- 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居世界前列
- 河南省民营企业贷款突破2.5万亿元
- 就业见习补贴怎么领取?权威解答
- 河南加快打造现代化消防安全治理体系
- 驻马店市银行业协会“十四五”工作交出亮眼成
- 平舆县人民检察院建立长效监督机制 督促扬尘
- 平凡的母亲
- “十四五”期间驻马店金融监管分局书写金融高
- “十四五”期间驻马店保险业发展步履稳健成绩
- 市生态环境局遂平分局压实主体责任 助企排忧
- 泌阳县绘就县域高质量发展新图景
- 驻马店市第十小学:杏坛育桃李 巾帼绽芳华
- 解码市第二人民医院系统化赋能基层“心”治理
- “翰墨寄乡情 丹青颂华章”赵尊清绘画捐赠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