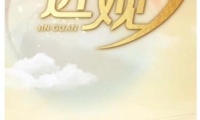家乡的雪
家乡的雪
□ 张富存
家乡的冬天,年年都会下雪。牛毛雪,松针雪,罗面雪,糁雪,籽雪,花瓣花;小雪,中雪,大雪,鹅毛大雪,斜斜密密,纷纷扬扬,飘飘洒洒,从深秋一直下到桃花开。
常常是,金秋十月,麦苗才刚苫严地皮,晚红薯还没有刨完,棉花田还没有弄净,雪就脚跟脚地撵来了。先是下细雨,等气温下降到一定程度时,北风就扯着脖子吼开了,云也越堆越厚,等风停了、云住了,雪就扭扭捏捏登场了。刚开始是雨夹雪,不多会儿,雪籽就呼呼啦啦地下响了。下雪籽最有意思,就像个顽皮的孩子,落在你的头上、脸上、嘴巴上、鼻子上,还总喜欢往你衣领子里钻,不疼,酥酥的,麻麻的,像是在与你亲昵。这是下雪的前奏,就像说书人说的书帽,大部头还在后面呢。等雪籽疯够了、玩累了、告一段落了,雪花就不紧不慢地漫天飞舞了。都说:十月天是妖婆脸,一天十八变,这话真没瞎说。在我们老家,至今还流传着一句“十月十五,冻死老妪”的老话。因为还处在深秋,并不是真正的冬天,树上大部分的叶子还没有落,恋秋的洋槐叶、柳叶、梧桐叶、柿树叶、银杏叶都还在绿着,雪落在上面,莹莹的,绿绿的;虚虚的,实实的,像笼了一层纱,梦幻般的,迷人极了。乡亲们可顾不上欣赏这些,一个个着急往地里跑,拿薄膜去苫白菜,扛着铁耙去扒红薯,晚的话就都冻烂在地里了。但冻坏红薯冻不坏粉子,雪过后,农人把红薯扒出来做成粉条,于是家家户户的院子里,都被白花花的粉条占满了,天地间又像下了一场“雪”。因为是一年里的第一次下雪,老百姓习惯叫它“第一场雪”,文雅点儿就叫它“初雪”。记得2008年,家乡第一场雪于农历九月十六就早早到来了。由于此时气温还不是太低,因此下的雪常常是小雪或是中雪。
气温继续下降,到了冬至节气,才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。早晨起来明晃晃的太阳还照着,哪像下雪的天,谁知到了中午,西北风一刮,漫天的大雪就随风飘扬了。这可忙坏了动物们,大尾巴的松鼠、花肚皮的喜鹊、青头绿屁股的蚂蚱,像是展开了竞赛,都在加紧搬运粮食。这场大雪,不知道还要持续多少天,不囤足粮食怎么能行。最轻闲的还数农人,地里的活儿都忙完了,晚红薯也刨光了,大白菜也下窖了,麦苗也都不缺吃不缺喝地在“家”安逸地猫冬呢。农人啊,真是赶上了好时代,村口的两间闲房子被他们腾腾当成老年俱乐部——一张破桌子、几条歪板凳,不知谁又抱来一掐子柴火,大爷大叔们围坐在一起唠嗑:张家又买轿车了,李家又在城里购房了,今年庄上新修的水泥路,明年还要打井架桥……家事国事天下事,如数家珍。大娘大嫂们围一圈儿,把刚才从雪地里弄的柴火掐过来,引着火,湿柴干柴不管,穰柴劈柴不管,呛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也不管,有凳子了搬个凳子,没凳子了屁股底下垫把柴火,烤着火,也不耽误大家呼呼啦啦地打开话匣子:南院家的小子今年就该结婚了,北院家的姑娘今年考上研究生了,谁谁家的闺女给她妈妈买一身新棉衣了,又是谁谁家的儿媳妇去年给她婆婆买的棉鞋还没有穿,今年买了新的又寄回来了……家长里短,门里门外,唠叨没完。雪花听到了,从门缝里挤进来,晃着圆圆的脑袋,嘻嘻地笑,好像在说:“都说天上美,来了才知道,还是乡间美啊!”
也有碰着干旱年份的,入冬后一直无雪,天干物燥,麦苗旱得苦愁着脸,大家急盼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雪来慰藉。你别急,不是还有一句俗语叫“大雪年年有,不在三九在四九”吗。到了数九寒天,冷空气活动频繁,天上的云朵变幻也快,没准哪一天,大雪说到就到了。大雪往往是从午后开始的。天气暖温温的,没有一丝风,天空像铅灰色的大幕,云朵越来越低,忽然一阵风,大雪就铺天盖地了。老套路了,起初是雪籽一粒一粒的,紧接着是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地从天空撒下。仔细看,雪籽的队伍里,还夹杂有碎屑,像牛毛、像花针、像松芥、像银丝,游游荡荡,飘飘忽忽。正迷茫时,一转眼,雪粒变成了雪花,先是一片一片的,似棉絮、似鹅毛、似桃花瓣,扯絮搓棉似的,不分路数地撒。霎时,天上、地上、树上、田野里,天地间一片白茫茫,分不清哪是边儿哪是沿儿。有时候什么征兆也没有,晚上睡觉时还是晴天,等第二天早上醒来,睁眼一看,屋里怎么亮堂堂的,好像黎明提前到来了。隔窗一瞧,咦,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好大的雪啊!“吱——”东院的门开了,“好雪!好雪!”张大伯望着大雪在笑。“呀——”西院的门开了,“吉雪!吉雪!”王大妈看着大雪在乐。出门走走,呜呜——大公鸡在白屋顶蹦跶着;喵喵——小花猫在院子里画梅花;咯咯——胖妞妞在雪地上留下一串小脚印。到村头溜溜,小路消失了,小河隐没了,田野盖着厚棉被睡着了,远山看不见了,枯树像仙翁,房子像漫画,偌大一个世界夸张得像童话。
九九歌中还有一句:五九六九蒸馍肉酒,意思是该过年了。雪姑娘也真善解人意,为了渲染节日气氛,也或许是为了沾沾人间喜气,常常在过年时不期而遇。雪姑娘来了,年味更浓了。就说赶年集吧,虽然雪深路滑,但咱老百姓不烦。闺女陪着母亲,媳妇伴着婆婆,一呲溜一滑地赶集。人可真多呀,热热闹闹,挤挤扛扛的,一家人走着、看着、商量着:鸡鸭鱼肉,葱姜蒜韭,牛奶鸡蛋,衣服鞋帽,这是基本,都得买;花生、瓜子、糖果也得买点儿,春联自然少不了,这是春节的标配……看差不多了,然后提着、背着、扛着、抬着,踩着雪,把装得满满一大车喜庆拉回家。再扯扯拜年走亲戚吧,不管风再大、雪再紧、路再滑,拜年的脚步是不会被隔断的。孩子们都放寒假了,疯呀、跑呀,打雪仗呀、抛雪球呀,闹翻天了,还有几个孩子拿起铁锨堆雪人,用辣椒当鼻子,再切两轱辘红萝卜当眼睛,衣服和鞋子都弄湿了,爸爸打,妈妈骂,打呀骂呀也不回家,只顾乐呢!年节里,年轻人都回来了,就以雪为媒吧,东家领着闺女,西家领着小子,选个吉日把亲事订了,两颗年轻的心就连在一起了。小村银装素裹,家家红灯高悬,户户红联崭崭,不知道是这圣洁的白彰显了这喜庆的红,还是这喜庆的红成就了这圣洁的白,只知道这一白一红相遇在春节这个时光节点,就如同阆苑遇见仙葩、美玉遇见无瑕,是那么相得益彰、舒心养眼。村中央,男人擂起了震天的大鼓,大姑娘、小媳妇扭起了秧歌,大家在“瑞雪兆丰年”的氛围中,笑着、唱着、舞着,此起彼伏的欢闹声在小村上空回荡。
九九歌里最后一句是七九八九抬头看柳。过罢年,气温上升,冰雪消融,杏树开花,柳树发芽。虽然打罢春了,但并不是说就不会下雪了,三月三还下桃花雪哩。“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”,是常有的事。因此,棉衣裳还不能脱,一旦有寒流活动,天气说变就变,这叫返春。但毕竟是春雪了,即使是大雪,也是下一阵子,不会持续多久,太阳一出,雪就化了。真正不下雪的日子,要等清明以后。有经验的老农都知道,清明断雪霜。过了清明,大地回春,万象更新,桃红柳绿,莺歌燕舞,麦苗返青,油菜金黄,一派春和景明,该上班上班、该打工打工、该上学上学,农人也发动起了拖拉机,准备春耕备播。学屋里坐着几个娃娃,正在摇头晃脑地背着书:我是一棵种子,春天到了,农民伯伯把我种在地里,我要发芽,我要开花,我要长大……
精彩推荐
- 西平县 精准解题促振兴
- 泌阳县以科创之力激活高质量发展新活力
- 宋艳丽:文旅融合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
- 正阳县高质量发展跑出“加速度”
- 遂平县 奏响生产“奋进曲” 交出发展“新答卷
- 陶庄村的乡风变化
- 116条通学定制公交专线折射“大民生”
- 我市5个集体、14名同志受中国关工委、河南省
- 爱上一扇窗 打开一扇门
- 我国下达2026年医保财政补助及建设资金4166亿
- 河南首份报关单证自助打印落地 企业尽享数字
- 刘阁街道清理整治农村道路 提升群众出行质量
- 驻马店:靶向施策破解就医难题 群众尽享“健
- 产业合作新阶段 卢森堡首批制造业项目在航空
- 11月份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平均
- 抗流感、重养生,巧用中医方法安度寒冬
- 史丹利复合肥让粮食吃上“好粮食”
- 驿城区 以助餐“小切口”做好养老“大文章”
- 市民政局发出“寒冬送温暖”倡议: 帮助每一
- 驿城区纪委监委强化纪律教育 培育廉洁新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