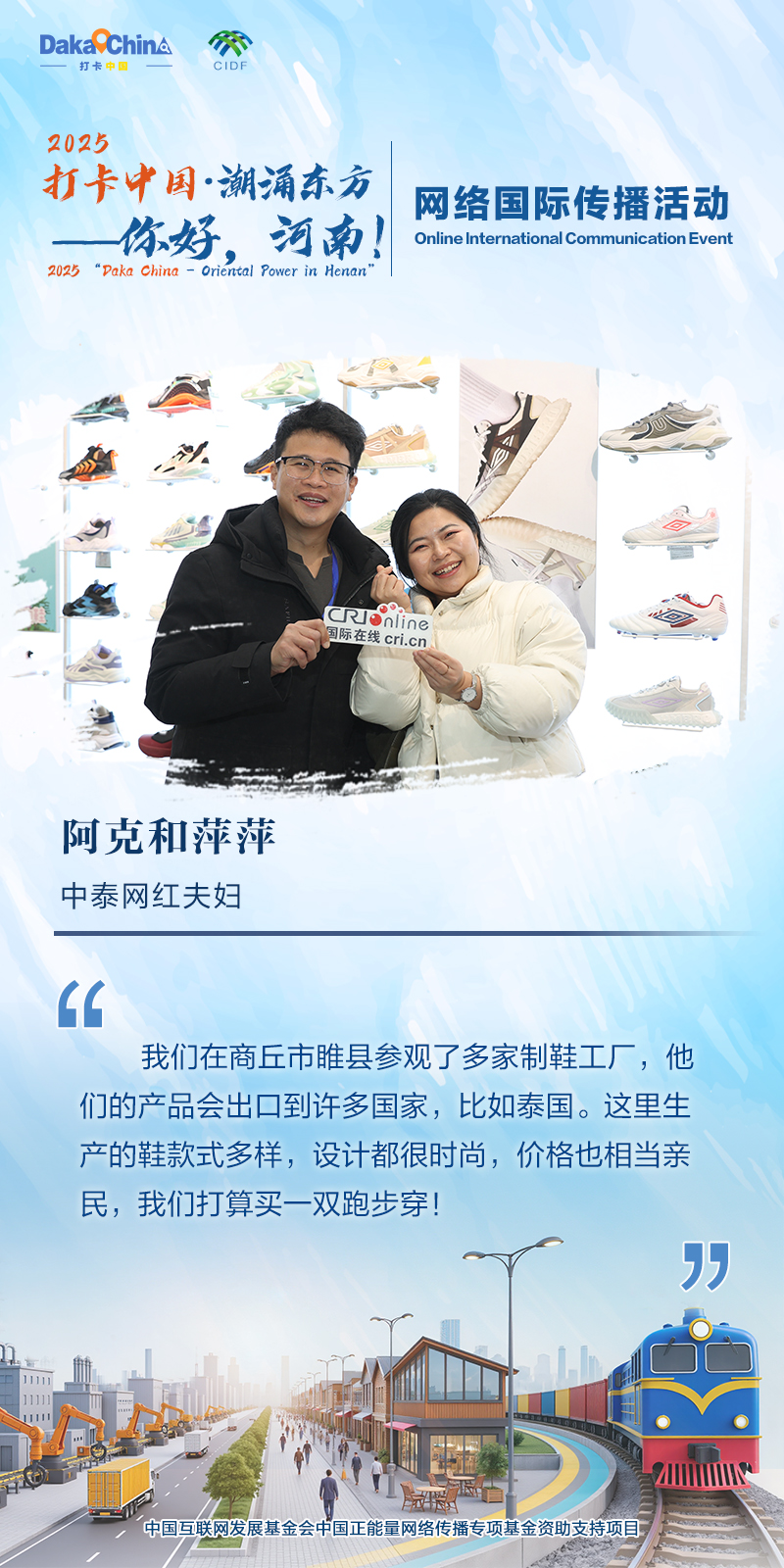游东营黄河入海口
游东营黄河入海口
文/郑松才
金秋时节,秋高气爽,我应邀参加由中华诗词杂志社主办的东营金秋诗会。诗会在东营宾馆召开,与会人员聆听导师们的诗词宏论。然而,诗友们更向往会间特意安排的去黄河口采风活动。
车子在公路上缓缓行驶着,两旁是无边的芦苇荡。九月的光景,芦苇正抽着银白的花穗,风一过,便漾成一片流动的雪原。间或有几株垂柳,绿意还未曾褪尽,柔柔地拂在水塘边。水是静的,映着高远的蓝天,却不时被惊起的水鸟划破。那是一些不知名的鸟,白的像云,灰的像雾,倏地掠过水面,消失在更深的芦苇丛里。
在鸟类博物馆里,我看到了东方白鹳的标本。它静静地立着,长喙如墨,羽翼似雪,眼神还留着荒原的风霜。后来在研究院的栏杆外,竟望见了三五只活的,在浅滩悠然踱步,时而仰颈长鸣,那声音清透得像要把秋空刺破似的。同行的诗友轻声吟道:“千年鹤壁三叠雪,万里云天一唳风。”我忽然觉得,这洁白的生灵,不正是黄河口最灵动的诗行么?
终于到了那块刻着“黄河入海口”的巨石前。朱红的字迹,在秋阳下灼灼地闪光,像是黄河最后的落款。登临观景台,浑黄的河水正浩浩汤汤地奔来,那样宽、那样浊,仿佛把整个黄土高原都搅碎了裹在怀中。风很大,吹得衣袂猎猎作响;河水拍岸的轰鸣,混着沙土的腥气,扑面而来。那是一种原始的、野蛮的力量,让你不由得想起“黄河西来决昆仑,咆哮万里触龙门”的诗句。
登上游轮时,天色愈发湛蓝了。船身破开波浪,渐渐驶向河海交汇之处。奇妙的是,那浑浊的黄河水与碧蓝的海水,竟不肯立刻相融。一边是厚重的黄,像陈年的绸缎;一边是透明的蓝,如初拭的琉璃。它们纠缠着、推挤着,在相接处划出一道蜿蜒的曲线,仿佛天地间最宏大的一幅水墨画。有位老先生扶着栏杆喃喃地说:“这哪里是汇入大海,分明是捧着万里黄土来朝贡啊。”
我忽然想起黄河的改道史。这条任性的巨龙,曾在华北平原上恣意摆动,北夺海河,南侵淮水,所过之处皆是泽国。直到1855年,它才择定眼前的河道,从此安澜入海。这多像漂泊的游子,历尽沧桑后,终于找到了归宿。它此刻的平静,底下该藏着多少颠沛的故事。
赤焰接海,碱蓬染秋,黄河口岸披红装。入海口滨海滩涂上,连绵不绝的盐地碱蓬焕发绛红,犹如火焰般热烈而鲜艳,在广袤的滩涂上形成“红地毯”般的壮丽景观。导游介绍,黄河入海口“红藻”现象,实为翘碱蓬在秋季从绿色转变为深红形成的自然现象,兼具生态和旅游价值。翘碱蓬不仅是生态系统健康演替的标志性物种,还为鸟类等众多生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,促进了生态多样性的保护。这一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,成为黄河入海口湿地生态旅游的一大亮点,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。有诗友戏说:“这是东营铺开红地毯在迎接我们吧!”于是大家齐咏起了诗人刘庆霖的诗句:“九月海风爽,东营待客忙。铺开红地毯,在此候朝阳。”
游轮划着大圆圈,几个小时的行程,把太阳赶向了西方。夕阳正把芦苇染成金红。湿地的水面浮光跃金,偶尔还有晚归的鸟群掠过。我想起日间见过的生态修复展板:退耕还湿,引水润泽,这片年轻的土地正重新焕发生机。黄河带来的泥沙每年仍在下游造出新的滩涂,那是最稚嫩的土地,也是最充满希望的田野。
“黄河落天走东海,万里写入胸怀间。”千年前李太白这样唱过。而今我站在黄河与大海的呼吸之间,忽然懂得了那种浩荡,不是征服、不是驯服,而是历经劫波后的相知相守,就像母亲额间的皱纹,浑浊里沉淀着清澈,沧桑中蕴含着新生。当游轮调头返航时,我最后回望那道黄蓝交汇的线,觉得它不再是分界,而是天地间最温柔的缝合。
精彩推荐
- 心智障碍青年“解锁”职业初体验
- 第27届中国农加会打造农产品加工“智慧盛宴”
- 正阳:传统鸭蛋成百姓致富“金蛋”
- 郭集镇大棚经济助力乡村振兴
- 时光里的针脚与烟火
- 瓦岗镇种植野菊花助力乡村振兴
- 箱包“天中造”破圈“贸全球”
- 新蔡县扎实推进“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”文明实
- 河南省全链条支持创新药产业高质量发展
- 危急时刻伸援手 凡人善举暖人心
- 两部门联合发布《寒衣节文明祭扫倡议书》
- 10月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
- 驻马店“十四五”应急管理答卷引发社会各界热
- 全运会冠军骆书艳载誉归来
- 未雨绸缪 安之若素
- 驿城区文化惠民工程彰显品牌效应
- 驻马店“十四五”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成效显著
- 科技赋能助力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
- 300余幅珍贵图片 展现驻马店60年辉煌成就
- 2025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 河南高校86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