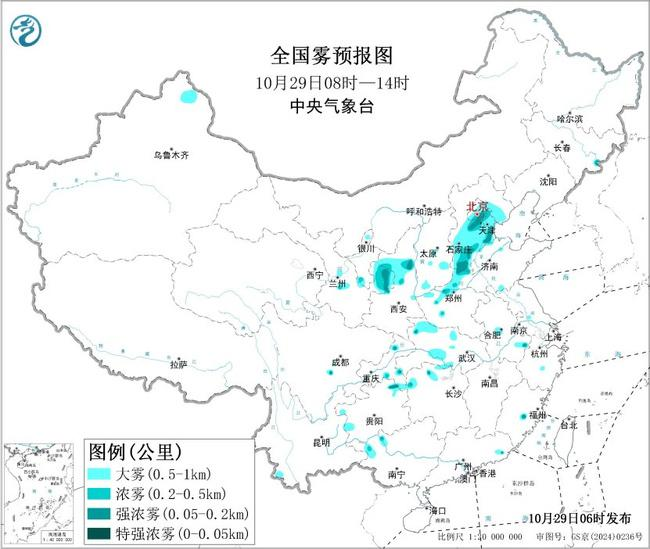柿子红了
柿子红了
□ 刘 慧
秋天是个多彩的季节。在我心目中,最夺目的颜色,当数深秋的那一抹红。
秋高气爽,当天地间只剩下疏朗的线条与灰蒙蒙的底色时,村前的那棵老柿树上便会高高地挑起一盏盏红灯笼。那红,不是娇嫩的粉红,也不是艳俗的朱红,而是一种经过风霜浸染、阳光曝晒后沉淀下来的、厚墩墩的绛红,像陈年的胭脂,又像温润的玛瑙,沉甸甸地压在近乎光秃的枝丫上,成了秋天这个萧瑟季节里唯一热烈得似乎要滚烫的燃烧。
老柿树是有灵性的,时常看见村里有人对着它喃喃低语。老柿树的树身很粗,两三个孩童拉起手方能将其合抱。树皮黝黑皴裂,像一部无字书,默默地见证过几代人的童年。我们那时是不大懂得敬畏的,心心念念的,是它带来的甜头。春天里,它开出些不起眼的淡黄色的小花,不久便结出青豆似的果子,风一吹,簌簌地落。我们女孩子蹲在树下,宝贝似的拾起来,用线绳串成项链、手钏,挂在脖上、手腕上,那青涩的凉意贴着皮肤,如同得到了最华美的装饰,美美的,仿佛人也变得漂亮了许多。
真正的冒险在秋天,当柿子刚泛起一层薄薄的黄时,我们这些小孩子肚子里的馋虫便被勾了出来。柿树是有人看管的,我们拿定主意趁中午没人时“偷袭”。几个小伙伴分工明确:机灵的放风,麻利的爬树,老实的在树下张着衣襟接柿子。攀树是需要勇气的,不单要防着被人发觉,更得提防树上的“洋辣子”。“洋辣子”是俗称,是一种虫子,色彩艳丽,却很“狠毒”,浑身支棱着一根根青刺,肌肤一碰,便是火辣辣的一道灼痕,疼得人直吸冷气。可为了那一点儿想象中的甜,这些小伤小痛便都顾不上了。
得手之后,我们躲到一个无人的角落,分享“战利品”。急急咬上一口,入口虽有一丝甜,旋即被一股涩涩的味道席卷了舌苔,仿佛整个嘴巴都被麻布裹住了,只得狼狈地吐掉,赶紧用牙齿不停地刮舌头。后来才知道,这样的生柿子是需“懒”过才能吃的。我见过母亲“懒”柿子,在锅里添上温水,将青黄的柿子浸入后,放置一阵子。这一阵子对我来说仿佛是最难熬的,围着锅台转了又转,一遍遍地询问母亲:“好了吗?”“快好了吗?”终于尝到了“懒”好的柿子,显然已褪尽了涩味,变得脆生生的,清甜爽口。只是,那些偷来的果实,是不敢拿回家让母亲发现的,尝着不是味儿便随手丢弃了。那些柿子多半被糟蹋了。怪不得那时村里人都不待见我们这些小孩子呢。
柿子真正熟透的时节,气氛便全然不同了。那是一种慷慨的、带着仪式感的分享。柿树叶几乎落尽,只剩下满树累累的纯粹的红,压弯了树枝,像要坠下来。这时,柿树的主人会喊来左邻右舍,一同分享这满树的果实。树上有人小心翼翼地摘,树下有人稳稳当当地接,生怕那红玛瑙摔在地上,迸裂了身子。裂了口的柿子很快会坏掉,不易存放。家里的大人跟着忙活儿一通后收获就来了:一堆柿子,熟透的,皮薄如纸,汁液饱满,需得用手轻轻捧着,在底部嘬开一个小口,那蜜样的、凉丝丝的果肉便喝进了嘴里。我们那儿不说吃柿子,而是说喝柿子。这个“喝”字,可能是因为柿子这如琼浆玉露般的口感而来的吧。未熟透的柿子,母亲便将它们温存地收藏起来,留着慢慢享用。
成家后,仿佛是为了寻个寄托,也在院里种了一棵柿树。它孱弱地长在院子的西南角,在被疏于管理的情形下,也能年年结几个果子,只是等不到红透,便被风扫落在地,化作成泥。不知是日子好了、嘴刁了,还是心境变了,那曾经视若珍宝的滋味,竟变得可有可无起来。
近两年,却莫名其妙地又馋起柿子,那一口软甜的滋味总在心头泛起。去超市买来,小心翼翼地剥开,将曾经熟悉的味道含在口中,竟有几分恍惚。又见市场上卖的新奇的、无核的小柿子,吃起来虽甜,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
前两天傍晚散步时,路过不知谁家的地头,猛地又瞧见一树灯笼似的小柿子倔强地挂在枝头。那浓烈、深邃的红,一下子牢牢吸引我的目光,勾起我的回忆,唤醒我沉睡已久的、甜甜的味觉。我立在那里,看了好一会儿。
精彩推荐
- 市文明办发出重阳敬老倡议
- 上蔡县:九九重阳“云”相约 拳拳孝心“网”
- 2025年河南省电商巧媳妇直播带货大赛举行 驻
- 柿子红了
- 构建全市媒体传播矩阵座谈会召开
- 驿城区:慰问演出传深情
- 确山县:情满重阳节 爱润孝心苑
- 强化服务优保障 守护幸福“夕阳红”
- 2025年驻马店市第一批诚信建设“红黑榜”名单
- 爱上野菊花
- 驿城区:志愿在行动 服务暖人心
- 文明新风润天中
- 驻马店市台联召开一届四次理事会
- 新蔡县人大常委会让代表履职“实”起来
- 全市宣传文化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
- 科技赋能产业焕新蝶变
- 正阳:畅通秸秆回收利用“绿色通道”
- 驻马店“十四五”文旅强市建设引各界热赞
-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举办2025年第四期“双月讲堂
- 驻马店海关精准施策助力加工贸易提档升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