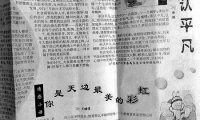馒头记
馒头记
文/刘慧
在俗话里,馒头被称为馍,馒头是馍的一个比较正式的说法。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南人,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馒头。如果每天不吃馒头的话,就会感觉少点什么。在我们这里,一般早晚吃两顿馒头,中午吃面条。馒头和面条都是面粉的产物,总之,面食颇受河南人青睐。
最喜欢吃自己动手发面,蒸出来的地锅馒头。掀开锅盖,热气腾腾的蒸气里,白白胖胖的馒头出锅了,不说味道,单单闻到那醇香的气味就是一种满足和享受。如果配上辣椒圈和蒜瓣,吃起来更叫一个过瘾。新蒸的馒头绵软,口感好,味道甜而发香,蒸一锅馒头,一顿肯定吃不完,剩下的就要馏着吃了。锅里添水,放上箅子,馒头放在箅子上,通过水蒸气把馒头重新加热。加热后的馒头口感仍很松软,若是反复加热的话,吃起来就不那么可口了。馏馒头没有蒸馒头费时,一般十来分钟就可以了。
再说下“馏布”的事。这还是方言。特意在百度上查了查,居然有它的解释:“馏布是一种传统的烹饪工具,主要用于蒸馒头、包子等面食时垫在笼屉上,以防止食物粘黏,通常由白色细纱布制成。也可在面团发酵和食物蒸制前覆盖,保持湿度并防止灰尘污染。”我补充一点,盛放馒头的筐子一般也用馏布盖着,作用同样是防尘和保湿。还有一种能够替代馏布的天然好物,就是玉米叶。玉米快要成熟的时候,需趁晴天,去田地里“打”(方言,摘取的意思)玉米叶,选干净宽长的,弄一些来,放在阳光下暴晒,晒干水分,两头用刀切整齐,一捆一捆扎好,找个通风的地方存放起来,随用随取。用玉米叶蒸出来的馒头有一种独特的味道。因此,在夏日里,家庭主妇们就把“打”玉米叶当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。
在那些物质匮乏的年月里,能吃上一口白面馒头简直是一种奢望。馒头的滋味,是苦涩日子里最真切的一丝甜头,是照亮漫漫长夜的一点微光。经历过饥馑的老一辈人,心底大都藏着一种对白面馒头近乎偏执的珍惜情结。这种情结,绵长而深刻,即便在今日富足的生活里,也未能完全抚平心底那一道饥饿的烙印,难以弥补生命中被亏欠的一段时光。我的老父亲便是如此。
如今,白面馒头不是什么稀罕物了,反而杂粮馒头被推崇。于是,窝窝头成了新宠,黑黑的,黄黄的,说是吃了对控制血糖和均衡营养有好处。有一次,我买馒头时挑选了几个杂面馒头,想换换口味儿。没想到,当我把一个杂面馒头递给老父亲时,他说:“不吃,不吃,小时候吃得够够的……”父亲还不爱吃买的馒头,他总说买来的馒头不好吃,不如自家地锅里蒸的馒头筋道有味儿。
每到年关,蒸馒头便成了每家每户的头等大事。那不再是日常的一锅两锅馒头,而是要蒸出足够吃到正月十五的“年馍”。那几天,左邻右舍常常互相帮忙,几家子的女主人围在一起,说笑着,手下却毫不耽搁,揉、搓、切、捏,一个个圆润的馒头从指间诞生。厨房里,烟雾缭绕,暖意融融,馒头里填满了最浓重、最朴实的年味儿,成了团圆、富足和美好祝愿的象征。
河南人对馒头的依赖,也衍生出许多智慧。隔夜的馒头,若是变硬了,除了馏,还有一种更妙的吃法——烤。放在炉火边,或用电饼铛慢慢烘烤,直到外皮变得金黄酥脆,用手指一弹,“嘣嘣”作响。掰开来,内里却还是柔软的。一口咬下,焦香与甜味在口中交织,再配上一碗稀饭(俗语,面糊做成的面汤),便是最简单也最熨帖的一顿饭。有时,也会将馒头切成片,用少许油煎至两面金黄,这便是香喷喷的“馒头片”,是许多孩子童年里最美味的零食。
远走他乡的游子,最大的念想,往往就是这一口淳朴的馒头。它不像异乡的点心那般精巧,却有着最扎实、最本真的力量。它安慰的不仅是肠胃,更是那漂泊在外的、思乡的味蕾。馒头放进汽车的后备箱里被带走,在他乡吃上一口,仿佛能让思绪瞬间穿越千山万水,回到那片依恋的土地上。
馒头,继承了一粒麦子的朴素,也用一颗朴素的心,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精彩推荐
- 境外间谍瞄准青年学生 国家安全部解析典型案
- 点燃“心青年”家庭的希望之火
- 蓝天碧水净土相伴 美丽驻马店生态惠民成色足
- 新蔡:让非遗传承点亮文化记忆
- 馒头记
- “十四五”期间驻马店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
- 我市收听收看全省森林防灭火暨冬春火灾防控工
- 房地产行业将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
- 11月1日起 驻马店推行7项交管便民新措施
- 河南车如何更好驶入拉美市场
- 2025年“119”消防宣传月消防安全知识有奖竞
- 市生态环境局平舆分局靶向治污护生态 守护碧
- 教育部发文 要求高校特殊类型招生严格报名资
- “豫排”能打又会玩 赛事经济含金量还在上升
- 6部门联合开展1年专项整治打击“黑救护”
- 驻马店首项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上线
- 贴息1%!河南推出“豫农担—救灾贷”为农护
- 驻马店首项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上线
- 春节假期共9天!2026年放假安排来了
- 前三季度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16.2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