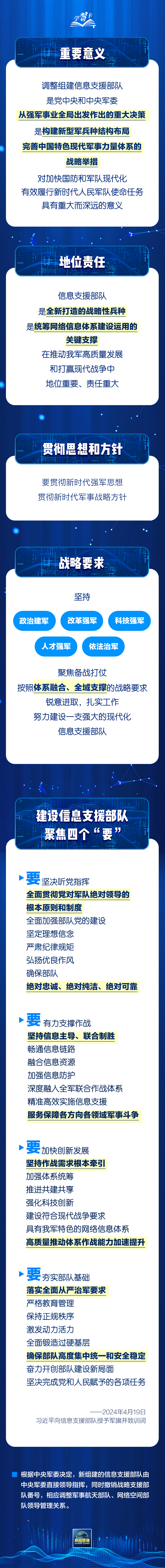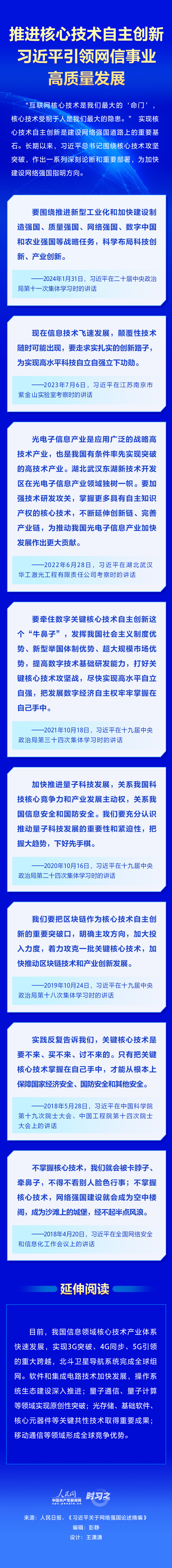一件灰西装
□董立伟
娘和新中国同岁,今年70岁了。娘结结实实病了一场,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,病情好转出院了。娘的目光一如既往地坚定、坚强,对生活充满无限的期待。
娘出院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让我陪她回老家一趟。我知道,娘离不开老宅和老屋,离不开爹当年植下的竹子,离不开老院子那满墙的丝瓜,离不开院墙下火红的鸡冠花……
娘在院子里转了一圈。我牵着她的手走进老屋,就像小时候娘牵着我的手走进当初新建的屋。娘在我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到东间老床前停下来。这张床是爹和娘当年的婚床。爹是木匠,当年为迎娶娘,亲自伐木做床。娘双目凝视着床头的大板箱,像在寻找遥远的记忆,那是娘结婚时唯一的嫁妆,娘平常不让我们碰它。大板箱上的黑漆已经斑驳,与其说是一件家具,不如说是一件历经沧桑的老古董。
娘用手指了指床头的大板箱,让我打开,把里面的东西晾晒一下。这件是爹结婚时穿的衣服,那件是大姐出生时穿的衣服,那个是二姐刚上小学时背的书包……在板箱最下面,我看到一件叠得整整齐齐旧得泛白的灰西装,我的双手一颤,娘扯布、裁衣、缝衣……往事历历在目。
小时候家里穷,兄弟姐妹多,我只能穿姐姐和哥哥穿不上的衣服,看上去不男不女的。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下午,我和一名男同学发生矛盾,他指着我身上带红花的衣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戏谑我:“不男不女,假妮子,小老婆……”
在全班同学的哄笑声中,我怒气冲冲跑回家,把书包重重一摔,扯下姐姐穿旧的衣服扔得远远的,睁大眼睛向爹娘怒吼道:“我要新衣服,不给我买,我就不上学了!”说完往被窝里一钻,撒起泼来,用不吃饭表示抗议。
天黑了,娘点起煤油灯,和爹坐在床头商量着:“孩他爹,伟长大了,知道好歹了。明天我带着伟到集上扯回来几尺布,给他做件新衣服吧!”
爹咳了两声,说:“中!”
爹声音不大,对我来说就是一颗定心丸。爹颤巍巍地从床铺的席下面拿出一个小布袋,认认真真打开一个节,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元钱,小心翼翼地递给娘。
“去吧,买好看的。”爹倒头睡了。我的身子紧紧贴着爹和娘,满怀期待,甜甜地进入梦乡。
第二天吃过早饭,娘牵着我的手,朝集市上走去。好一个唯美的春天!油菜花恣意开放,朵朵碎花像孩子们心目中的童话,流光溢彩。麦子攒集全身的力量像拔河比赛的孩子一样向上拔节。南归的小鸟歌声嘹亮,划过美丽的弧线融进太阳的明亮。一路上,娘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,讲3年自然灾害,讲大集体,讲联产承包……
一块银灰色的布从集市上扯回来了。娘一手拿着尺子,一手拿着粉笔头,在我身上量来量去。一把剪子在布料上飞舞,一块块身体形状的布料叠放在缝纫机上。娘穿针引线,左手转动缝纫机轮,右手按住线脚,双脚不停地踩。
天慢慢黑了,娘破例点了两盏煤油灯赶做衣服。春天的月光像娘的爱一样富有诗意,碎银般地透过窗户洒在缝纫机上,洒在娘一丝不苟的脸上。夜风吹来,煤油灯的黑烟随风曼舞。我双手托腮,凝视着洒满月光的娘的脸。我深深吸着气,把春天的味道、月光的味道、布料的味道、娘的味道深深吸进。
星期一,我穿着娘为我做的新衣服——一件时髦的银灰色西装,顾不得欣赏春天早晨的美景,游云般来到学校,自信地在同学面前走来走去。这件灰西装装饰了我童年的梦想。
每个星期一,每次发奖的日子,我都穿着这件灰西装。这件衣服像岁月的诗歌,陪我走过朝朝暮暮,春夏秋冬,伴我取得一次次优异成绩,陪我走过两年幸福时光。
慢慢地,这件衣服像生命一样老了,旧了,瘦了,小了,更可悲的是上体育课时,我不小心划破一个长口子。娘穿针引线,在太阳下认真缝补起来。但我不再接受这件面目全非的灰西装了。
每当割草、铡草、喂牛、收割庄稼及准备过年炸肉、扫灶的时候,娘都穿着它,一直穿到褪色……
娘和新中国同岁,和新中国一样历经苦难。一辈子相夫教子、勤俭持家,用自己的善良和辛苦给孩子们铺就成长之路,为自己和孩子们留下了美好回忆。
精彩推荐
-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
- 推进“九大产业集群”高质量发展 更好助力现
- 遂平县营商环境再优化项目建设掀高潮
-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主任会议召开
- 新华社河南分社调研组 到我市采访调研
- 线上线下齐发力 为民办事提效率
- 强化责任 细化措施 确保2024中国山马越野 系
- 父亲的洋槐花
- 计划招聘966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- 泌阳县香瓜种植助力乡村振兴
- 9家景区免收首道大门入园门票
- 西平县供销社聚焦主责主业 做优为农惠农
- 驻马店智慧岛科创新城建设项目开工
- 教育部:高校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提前谋
- 2024年驻马店市机关党的工作会议召开
- 擦亮生态底色 徜徉“诗和远方”
- 5月1日起不再主动颁发纸质版不动产权证
- 要以高质量审计监督 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
- 李跃勇率队赴郑考察中原科技城和省医学科学院
- 河南自贸试验区进出口实现开门红